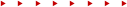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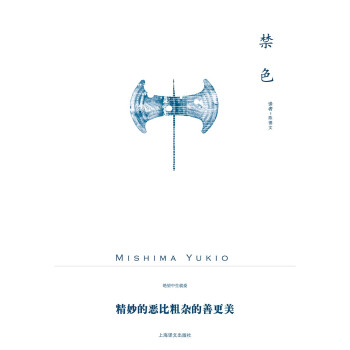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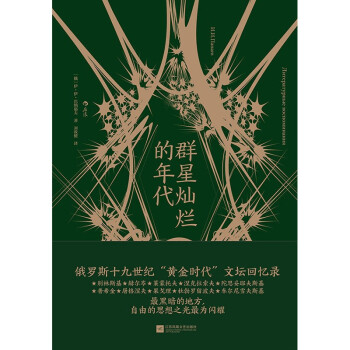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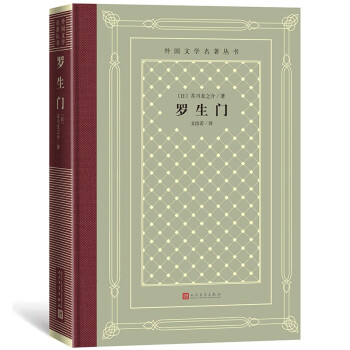




我在学校前车站下车时,听到车站旁边搬运公司办事处屋顶上,及早消融的雪水流泻下来。我只认为那是光的流泻。鞋底带来的污泥,在水泥地面涂上一片虚假的泥泞。那光一面一次次大声呼喊;一面投向那“虚假的泥泞”坠身而死。一道光错误地投身于我的脖颈……
校门内还没有一个人影。存物间也上着锁。
我打开二年级一楼教室的窗户,眺望森林的雪景。森林的斜面有一条小径,由学校后门向上通往这座校舍。雪面上的巨大脚印,沿着这条小径一直抵达窗下。足印在窗边折返回去,消失在左侧斜面看来是科学教室的一座建筑物后头。
似乎有人来了。从后门上来,瞅瞅教室的窗户,看到没有人,就独自向科学教室后面走去。后门几乎没有学生通过,风闻只有那个近江,来往于女人家时经过这里。不过,只有整队时才能看到他的身影。不是他又能是谁呢?这么大的脚印,只有他才有。
我从窗户探出身子,凝神望着印着这种脚印的黑土鲜润的色调。看上去,那是步履坚定、充满力量的脚印。那股无可形容的力量,将我引向那双脚印。我真想倒竖身子,沉落地面,将脸孔埋在那双脚印之中。可是,我的迟钝的运动神经,照例有利于我的自保,我把书包放在课桌上,慢腾腾爬上窗棂。制服胸前的暗扣抵在石造的窗棂上,蹭着我脆弱的肋骨,那里感觉到一种混合着疼痛的悲哀的甘甜。我翻越窗户跳到雪地上时,轻微的痛楚使得胸脯一阵快活地紧缩,同时充满战栗的危险的情绪。我悄悄将自己的套鞋,合在那双脚印之上。
巨大的脚印几乎和我的相同。我忘记了,这双脚印的主人或许穿着我们之间时兴的套鞋吧。看来,那脚印似乎不是近江的——追寻黑色的脚印,或许会背叛我当前的期望,但即便处于这种不安的期望中,也有某种东西使我着迷。此时的近江,已成为我期望中的一部分,对于先我而来,及早在雪地上印下脚印的那个人,我抱有为某种被侵犯的未知而复仇的憧憬,这种憧憬抑或紧紧抓住了我。
我气喘吁吁地追寻那道鞋印。
犹如跳过一块块脚踏石,鞋印顺次印在各种地方,有的是黝黑而鲜润的泥土,有的是干枯的草地,有的是结实的污雪,有的是石板小路。走着走着,我不由也和近江完全一样,迈开了大步。
我走过科教室后边的背阴处,来到广阔的运动场前边的高台。三百米的椭圆形跑道,以及围在跑道内的各个场地,一律包裹在闪闪的白雪之中。广场一角,并立着两棵高大的榉树,在晨光里伸展着长长的树影,为雪景别添一种朗朗谬误的意味——即便冒犯伟大也在所不顾。大树凭借冬日的蓝天和地面的雪光以及侧面的朝阳,以可塑的致密高高耸立,干枯的树梢和开裂的树干,时时掉落下来金沙般的雪粉。运动场对面并排着的一栋栋少年宿舍以及毗连的杂木林,依然一动不动地沉睡,似乎一丝微音也会引起广袤无边的反响。

温馨提示:请使用石家庄市图书馆的读者帐号和密码进行登录
